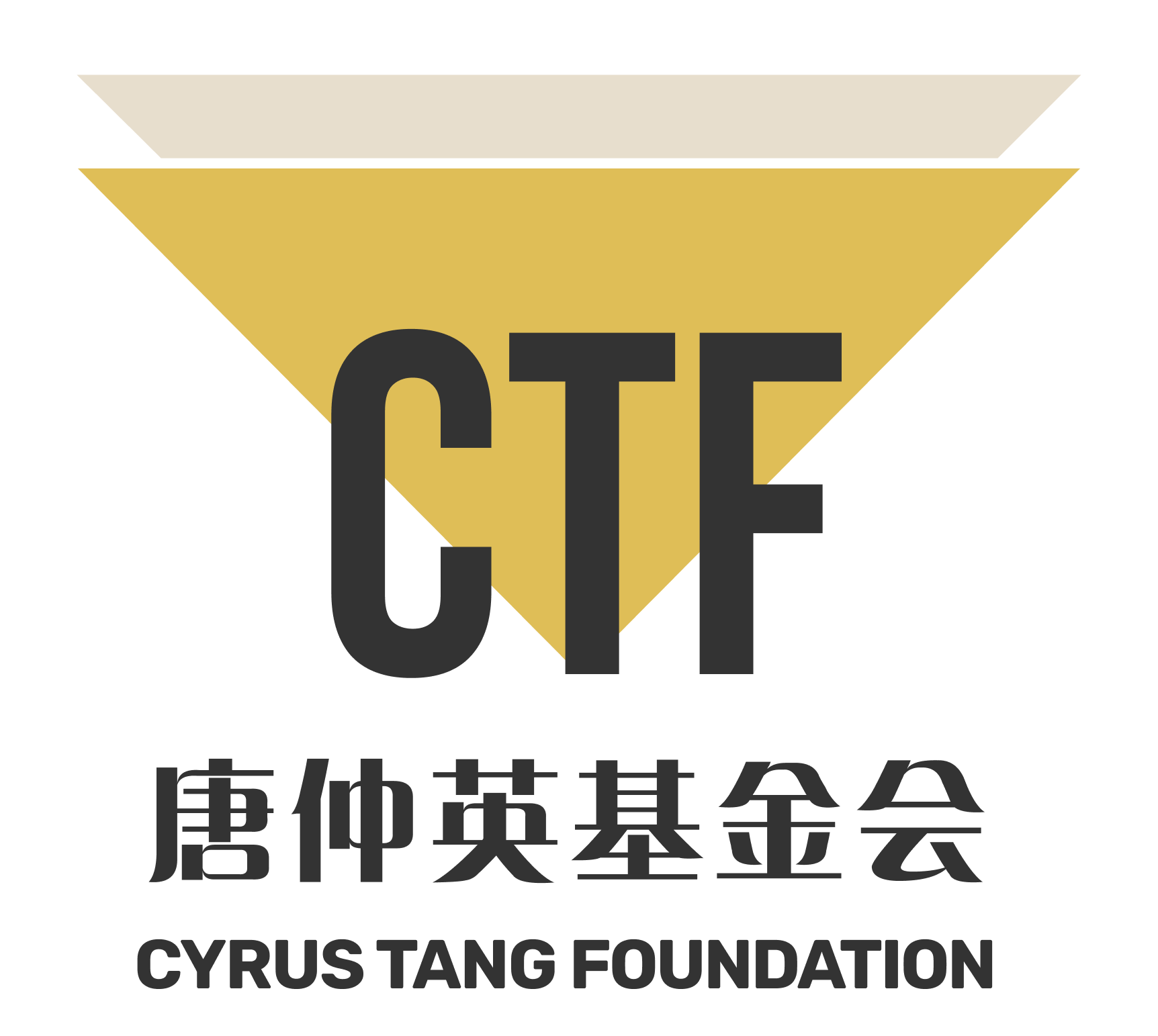巴西行记(节选)——北大2004届毕业生章邵增
巴西行记之一:
关于巴西人怎么吃香蕉和中国人怎么做贵族
2008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巴西。9月初回到美国,偶然打开《南方周末》的网络版来看,看到9月8日的生活版有一个专题,《寻访中国的“尖头鳗”》(http://www.infzm.com/content/16947,http://www.infzm.com/content/16964)。“尖头鳗”来自英文的gentleman一词,即所谓“贵族绅士”。该文出言必引所谓伦敦的老牌绅士杂志《GQ》,出语必称该杂志主编的所谓英国绅士幽默;大谈所谓西方文化中的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意指当今中国人日渐富裕,该怎样提升精神层面,学做优雅的贵族和绅士,比如“在西餐厅怎么点菜”、比如“血液里面带着贵气的男人”怎么“文质彬彬地品着香槟谈女人”,等等。我对西餐厅、香槟和女人这些本身是没有偏见的,甚至也是喜欢的。只是这文章摆出一副要引领中国人做贵族绅士的派头,内容却浅薄、盲目地紧,让我这个出生成长在中国农村、血液里肯定没有贵气的典型草根土包子读了之后颇有些不快。当年钱钟书在其名作《围城》里面将gentleman一词翻译做“尖头鳗”,来调笑当时崇洋媚外的所谓中国上流社会;今天我不怕狗尾续貂,也要调笑一下这新一波的邯郸学步的“尖头鳗”。
这个文章先是引述了英国绅士做派的遗老约翰•莫根(John Morgan, 1959-2000)关于如何吃香蕉的礼仪:“把香蕉横放在盘子上,用刀叉先将它的两头切去,然后再横向剖开香蕉皮,其后才将香蕉切成小块,优雅地送入口中……”并悻悻地说现代绅士不复如此,然后开始追寻现代西方绅士文化“在新时代的崭新面貌”。看到这一段,我猛然就想起上个月在巴西之所见,不禁哑然失笑。
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我在巴西的一家点心店吃早餐,看见一位老先生正是如此“优雅”地吃香蕉的,毫无二致。当时我惊异得很,所以自始自终地看着他吃完香蕉。此后我也见到了更多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巴西人如此吃香蕉,生香蕉熟香蕉都遵此法。莫不是这英国绅士精神的经典却在此传承?那南方周末的编辑和文章作者是不是应该来此地现场观摩一下这标准的维多利亚时代绅士风度?
等我把这一幕的镜头稍微放大一点,你或许也会会心而笑的。这个点心店位于巴西东北部城市Salvador最老也最破旧的街区“Dois de Julho”(意即“七月二日”,以重要纪念日或节日来命名街区或道路在巴西是很常见的)。这样的点心店(Lanchonete)在巴西遍布大街小巷,属于档次颇低的餐饮场所,点心、咖啡、果汁都是现成的,价格也便宜,很多巴西老百姓便在这样的点心店吃早餐,有的白领阶层也在装修和卫生稍好的这类店里吃早餐。我所说的这家小店在同行里面算是中档,来吃东西的都是附近的中下层老百姓,摆摊卖水果的、扫大街的,开小货车的……,而且几乎所有人的装束都是夹指拖鞋和短裤短袖。我说的这位老先生皮肤黝黑、头发灰白、胡子拉碴、T恤已洗到褪色,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一只脚在高处一只脚在低处,一边吃一边跟小店老板聊天,偶尔还跟小店门口路过的人高声打招呼。若是那约翰•莫根活过来见到这巴西“糟老头”如此“作践”他毕生倡导的绅士礼仪,估计会再一次被气死。
再说这巴西其实也是有种族和地域歧视的。这些皮肤黝黑的“东北人”便是被巴西其他地方人、尤其是巴西东南部和南部白人所鄙夷的,一则因为历史,“东北人”是巴西殖民地历史上葡萄牙殖民者和黑人奴隶或土著印第安人的“杂种”后代,二则因为现实,“东北人”往往比较穷,缺乏好的教育,更侈谈什么学习和继承绅士礼仪了。可是为什么这位老先生以及很多的巴西人会习惯于这样吃香蕉呢?那还得稍微讲讲巴西的历史和地理。
自1500年巴西“被发现”之后,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越来越多地来到巴西:殖民政府官员、商人、奴隶主、种植园主、以及在欧洲混不下去而来巴西寻找财富(如金矿)投机者和混混。在巴西独立(1822年)之前甚至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巴西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鲜明的殖民地特点,这里仅择要而述。关于经济,其宗主国葡萄牙并无意真正发展巴西的经济,而只是尽可能多快好省地榨取巴西的资源和财富,如矿产、木材和肥沃(但脆弱)的热带雨林表层土(用于大规模种植甘蔗和咖啡等欧洲消费品)。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经营主要在其大规模工业革命之前,其殖民地主要是作为贵族消费品的来源,而非工业生产原料产地,更不必适度发展殖民地经济和提高殖民地生活水平来倾销宗主国的工业产品;二是葡萄牙的主要商业活动是与东方的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进行的,巴西其实算不上葡萄牙殖民帝国经济的重点。因而葡萄牙人在巴西从事的是极其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包括后来引入的欧洲下层白人在内,他们的经济活动可以以“快钱”两个字来概括,而他们的形象可以“寻宝人”(Bandeirante)来代表。Bandeirante一词来自于葡萄牙语单词Bandeira,意思是“旗帜”,但是这里特指那些或在殖民政府、大商人(奴隶主和种植园主)的支持下,或自我组织的“寻宝队”的领头小旗子,跟在这小旗子后面的队员,都是Bandeirante(寻宝人)。这小旗子所号召之下的活动主要包括:寻找贵金属矿藏(主要是金矿)、寻找巴西木(Pau-Brasil,一种上好木料,巴西国名的来源)、寻找适于种植园的土地、捕猎逃亡的黑奴、猎杀土著印第安人以获得土地和奴隶,等等。无论哪一种活动,一旦成功,就财源滚滚;因为这是对所谓“无主”资源(包括奴隶)的直接占有,这财富自然是来得容易,所以叫做“快钱”。那这钱怎么花呢?最紧要的是两件事:一是建立自己的种植园,二是从欧洲运一个白人女人来做妻子。然后慢慢开始建巴洛克式的豪宅,添置精美的家具和餐具,开始出入歌剧院和高级俱乐部……一句话,就是追求在欧洲无法实现的贵族梦想。“寻宝人”出身的暴发户如此,社会地位较高的殖民官员及其后代因为忌讳被欧洲人视为蛮荒之地谋生的人,也是如此。稍有能力的父母们,都把子女送到欧洲去学习“先进知识”和贵族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信奉欧洲贵族文化,一方面是因为宗主国葡萄牙禁止在巴西设置中学及以上的教育机构,通过对殖民地子弟灌输宗主国的观念来维持对殖民地的政治和文化控制。
巴西的这种在“快钱”积累基础上的欧洲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在巴西的大城市中,有不少留存至今的20世纪之前的建筑,包括政府议会大楼、富人宅第、宾馆、歌剧院等,忠实地保存着欧洲17--19世纪的主要建筑风格,其中尤以各大城市的歌剧院最为美仑美奂,体现着那个时代巴西人的对欧洲贵族文化的执著追求,也展示着那个时代简单掠夺式经济活动所能积累的财富规模。而富裕阶层的这种贵族生活方式,同时也激励着几个世纪的巴西人对“快钱”的向往和追求。而偏偏巴西却拥有世界各国无可比拟的丰富自然资源,在耗尽了巴西东海岸上万公里长、数百公里宽的“亚特兰大森林”(以至于今天鲜有人知道其存在),却还有更为广袤的亚马孙大森林;巴西东南部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州因其矿产丰富,而直接被命名为“矿产州”(Minas Gerais),而至今巴西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矿产出口国之一;实在受上天眷顾,以至于巴西人颇带自豪地自我调侃“上帝是巴西人”(O Deus é brasileiro)。可是,也正是其貌似无穷无尽的资源,使得“简单挣快钱、过贵族生活”这一思维模式在巴西延续几个世纪而不灭。直至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贵族生活方式的追求在巴西人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如中上阶层对去剧院看演出的钟爱,再如家庭主妇对精美和繁复的家具、餐具的热爱,直至普通人优雅地用刀叉吃香蕉、比萨饼和烤鸡翅,凡此种种。而另一方面,在今天的巴西,需要定期焚毁原始森林的种植园农业仍是举足轻重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力量,一朝赢得选举便出售手中权力致富的政客大家都觉得稀松平常,傍富翁或傍富婆也不再是新闻,如此等等(是不是觉得这景象与今日的中国异曲同工?下文会有详述)。
而正如南方周末的专题文章所悻悻然地,在贵族生活方式的起源地欧洲,那些“现代绅士们”也不再用刀叉吃香蕉和比萨饼了;在号称最为发达和富足的美国,我也是从没见过。(我这里说的是欧美的普通人,欧美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我并不了解。)当然,各国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在今天不过是多元化的现实,其本身没有什么优劣或对错可言,不过这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脉络,确实值得我们----开始走向富裕、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的中国人----加以思考和借鉴的。
巴西学者Vianna Moog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书《寻宝人和开拓者》(“Bandeirantes e Pioneiros”),对巴西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在巴西和美国的学术界一度很有影响力,甚至引发了巴西公众的思考和讨论。这本书的起始问题是当时乃至现在仍然广为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巴西和美国,同样是两个“新大陆”国家,都曾为欧洲殖民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独立国家,幅员相当,都是移民国家,人口数量和构成也相当(人口构成:作为主体的白人殖民者后代+数量较大的黑人奴隶后代+少量土著印第安人+各种混血后代),而且巴西显然拥有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为什么美国在独立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之好,而巴西则相对要落后得多?在Vianna Moog之前,学者和公众已有过各种解释,如种族主义的解释:美国人的盎格鲁-萨克逊血统比巴西人的葡萄牙语血统要更加高贵、聪明和勤劳,或者说巴西的混血人口太多,从而削弱了白人血统的优势;也有宗教的解释:在巴西占主导的天主教崇尚对神的物质奉献、现世的宗教修为和死后的天堂生活,而在美国占主导的基督新教崇尚通过劳动积累尽可能多的财富,因为这本身即是对神的荣耀;也有地理的解释,如位于北半球的美国与欧洲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具有距离上的优势,或者说巴西的热带气候导致疾病盛行、土壤贫瘠、人民懒惰等。而Vianna Moog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大意就是:美国人具有一种开拓者的精神,从殖民地时期开始而尤其是独立之后,美国人对国土尤其是西部的开拓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所以他们爱惜自己的土地以及地上地下的资源,他们热衷于积累财富,因而日渐民富国强;而巴西人,正如我上文所述,则总是带着“寻宝人”(Bandeirante)的投机心态,寻找现成的财富,直接挥霍于对欧洲式贵族生活的追求,能够建成号称“南美巴黎”的繁华城市里约热内卢,却只是金字塔尖的欧洲中世纪式贵族生活的再现,却难以实现国民整体的富强。而这两种民族精神的差异来自于两个民族的形成过程的差异:美国人的民族主体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和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期来到美国的,并且带着基督新教中勤劳节俭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巴西人的主体形成之时,其宗主国葡萄牙尚未经历工业革命,仍然推崇欧洲中世纪式的贵族生活方式,“寻宝人”的投机心态正是中下层人民的贵族生活理想和巴西自然资源条件结合之下的产物。出于这样的国民心态,巴西的精英阶层人口所得以实现富裕的贵族式生活,而广大的下层人民却都处于贫困的状态。以简单攫取自然资源和剥削下层劳动力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无法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尤其是二战之后以技术和资本为基础的国家经济竞争力----,自然也无法实现美国式的持续和全面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
Vianna Moog的这本书是在二战后巴西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渴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的背景之下写成,不仅对巴西的殖民地历史和国民精神做出了深刻的批评和反省,而且也间接提出了巴西经济发展和国民精神转变的方向,是很适得其时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经历了著名的十年“经济奇迹”,虽然这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又一轮巨大消耗,但也开始了巴西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上的开拓,如世界排名第四的飞机制造公司,巴西的Embraer公司就是在这期间成立和壮大的。我不是说Vianna Moog的这本书导致了此后的经济大发展,而是说,诸如Vianna Moog这样的有识之士对本国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反思是此后巴西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当然也不乏对这本书的批评,对美国历史略有了解的人可能都会说,美国人也没有Vianna Moog所说的那么完美吧?他们当年不也是残酷虐待黑人奴隶、野蛮猎杀土著印第安人……这一点我完全赞同,还有更近的例子,如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加工业丑闻、涸泽而渔式的利用自然资源而导致的20世纪30年代肆虐美国中西部的黑风暴(“Black Bowl”,即沙尘暴),等等,都暴露了美国人同样也进行着掠夺式的“快钱”经济。而另一方面,巴西人也并没有Vianna Moog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堪。正如欧洲十八世纪一度盛行的“高贵的蛮族”(Noble Savage)的观念,其实大部分阐述这一观念的学者并没有见过美洲或太平洋岛屿上的“蛮族”;这一观念的出现显然带着对异族的浪漫化想象,其主要的意义在于反过来批评自身社会的弊病。当时欧洲的主要弊病就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传统社会道德败坏,而诸如“高贵的蛮族”之观念所引出的各种批评也间接地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调整。在我看来Vianna Moog的《寻宝人和开拓者》一书在我看来就类似于这一批判手法,也起到了其时其地的现实意义,因此不必苛求其面面俱到地呈现巴西社会,至于对其次要探讨对象美国社会就更不必了。)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人要做“贵族绅士”这件事情。简单地讲,巴西人在历史上对西方贵族生活方式的追求不可谓不努力,其追求基于殖民地经济制度和巴西丰富的自然资源之上,又反过来鼓励着在此基础上的“快钱”式的经济行为和社会政治文化。而其结果是,几百年后,巴西社会高度两极分化,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虽学得了贵族生活方式的一些皮毛,如用刀叉吃香蕉,却从未过上真正富足的生活;占人口少数的中上阶层虽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是因为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贫困和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小区和房子加上好几道铁栏铁窗还有报警器和门卫,夏天傍晚在街上开车再热也不敢开车窗,以至于他们自己都觉得像生活在监狱里一样-----这样的状态离当初所追求的优雅和绅士风度实在是谬之千里了。而本文第2页末尾所描述的当今巴西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颇有异曲同工之悲:高消耗、高污染的工(农)业生产,权钱交易和政商腐败,以及普遍的拜金主义。那么巴西人今天的“贵族式生活”也会在中国社会中出现吗?《南方周末》的专题文章所倡导的名牌消费、声色犬马的贵族绅士风度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作如此倡导,我很难想象对普通百姓没有负面的示范效应,进而对上述的这些问题没有推波助澜的恶化作用。
我上面这句话可能乍看起来很不公平:那《南方周末》的文章明明说了绅士风度是要“内外兼修”的,我怎么只片面抓住其外在追求(名牌消费、声色犬马)就大肆挞伐呢?片面抓住贵族绅士的外在追求的,实在不是我,而正是这个文章本身,尤其是这种倡导所带来最有可能的结果。
如《南方周末》文章所提到的,西方的贵族绅士文化源自于英国的等级制度。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英国的社会结构基本稳定在三个等级:贵族绅士阶层(Gentry Class),市民阶层(Burghers Class)和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或者简单地称作上层、中层和下层。这三个阶层的人从小就去不同的学校、受不同的教育,长大之后从事不同的行业、参加各自的社交俱乐部,阶层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晰。而这所谓的英国绅士(English Gentleman)的概念就是这个等级结构所框定的,一位英国绅士的塑造也是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成长和生活过程所产生的:只有上层和少部分中层男性按照其阶层所限定的生活方式生活才有可能成为绅士,下层老百姓和大部分中层男性哪怕再有钱也是不能被称为绅士的,除非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而获得女王的封爵。而巴西长期以来的社会结构也正是这样的金字塔形,只有金字塔尖的少部分人才有可能过上贵族绅士般的生活----只不过在巴西,进入贵族绅士阶层的门槛基本上变成了只有金钱而已。那么我们中国人要学习怎样的贵族绅士精神呢?是要在今日中国也形成一种稳定严格的等级分隔然后“长期熏陶”出“血液里带着贵气”的绅士吗?还是要鼓励不择手段地追求“快钱”和暴富然后去模仿殖民地宗主国的贵族文化?
这个文章也说到,“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绅士文化就已经发展成熟,它的核心包括自由的思想、公平合理的竞争原则、勇敢的骑士气概、务实的精神、高雅的艺术修养和得体的举止。”可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英国的绅士文化偏偏是在“日不落”殖民帝国最为强盛的时候而成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葡萄牙的贵族文化也是在其殖民帝国最为强盛的时候而辉煌?难道只是巧合么?有没有这所谓绅士文化的核心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以所谓“勇敢的骑士气概”为例。维多利亚时期绅士阶层的不少男性要去参军打仗或者治理征服的土地,贵族绅士的勇敢在根本上乃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开疆拓土和殖民统治。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他们来到中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倾销英国的工业产品,他们来到中国的圆明园和紫禁城抢掠中国国宝来丰富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这些人就是当时至为“勇敢”的英国绅士。再看看巴西的历史,那些参加“寻宝队”远征的巴西人要面对黑奴和印第安人的反抗、森林里豺狼虎豹蛇鼠毒虫的攻击和无止境的热带疾病的肆虐。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需要“勇敢”的气概,而与英国绅士不同的是他们主要的是出于为个人和家庭的富有和进入“贵族绅士”阶层。那么我们中国人今天要学习怎样的勇敢气概和贵族绅士精神?是为了建立殖民帝国世界霸权而去烧杀抢掠吗?是要为了个人和家庭的暴富而涸泽而渔、扼杀他人甚至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吗?
《南方周末》的这个文章虽然提到了一点风花雪月式的英国历史,虽然借了几个诸如“内外兼修”这样华而不实的词句,但是却没有稍加思考和分析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的现实意义,空泛地讲内外兼修却不看这“内修”所根植的当时当地的背景。这样去学所谓“贵族绅士”文化,所学到的难免不过是名牌消费、声色犬马之类的外在追求而已。
当然,这个文章只抓着贵族绅士的外在追求还有一个看似简单其时可能更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其文稿来自于《Magazine•名牌》杂志(英文单词“Magazine”的意思就是“杂志”)。那么这文章的鼓吹消费主义的倾向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不容易理解的是,这文章里面透露的一些论调实在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中西文化糟粕,比如关于女性,既有对1949年前有钱人三妻四妾的褒扬之意,也有将女性身体物化的暗示,实在是与这文章所盲目崇拜的西方贵族绅士文化中排除女性的传统有承前启后之殇。而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欧美,这样其实女性的论调早就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在今天的中国,男女平等的观念,自从民国时放了小脚、毛泽东指出“妇女能顶半边天”之后,更是深入人心。当然,我写本文远不只在于批评《南方周末》这篇文章的消费主义倾向,而希望为我们中国人思考在开始日渐富裕之后,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心态,或应该做什么样的绅士这一问题,提供更为广阔的参考视角。
巴西行记之三:
音乐与历史的二重奏:亚马逊剧院
2009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巴西的玛瑙斯(Manaus)市。Manaus位于巴西的北部,整个亚马逊大森林的正中间,亚马逊河的岸上。这个城市有两百多万人口,是巴西第八大城市,不过连巴西人自己都说这个城市比较脏比较乱。有一次,一个巴西朋友跟我说,Manaus这个城市规划不大好;因为跟他已经比较熟,我半开玩笑地回应,与其说是规划得不好,不如说是(没有规划)自然地摊大饼摊出来的。
带着游客的心态(虽然是工作的名义来的),我选了市中心一家老房子改造的小旅馆住着。因为Manaus的市中心(葡语:Centro)是历史古城区,建筑风格还蛮别致的。这个选择挺明智的,这一带虽比不上最新的城区整洁,满眼尽是高低新旧不一的老房子,有的老房子其实只剩了几根巴洛克式的柱子和爬了藤蔓的一两面墙——却倒也给人很坦然的真实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市中心的精华又在于圣•塞巴斯提翁广场(Praça de São Sebastião)。广场并不大,西面就是著名的亚马逊剧院(Teatro Amazonas),西北角是圣•塞巴斯提翁教堂,广场的东南北面则以各色酒吧餐馆为多,兼有几家画廊和工艺品店,广场的中间有一些树和长椅。在位于热带雨林地区的Manaus,白天是谈不上什么室外活动的,不过每天从傍晚开始,这个广场就热闹起来了。先是日落时分酒吧的服务员们就把桌子椅子都放到广场上来,广场的东南角摆上了一个小舞台音响设备和很多的椅子,然后广场中间的树荫下长椅上就来了歇脚的、乘凉的、谈恋爱的各色人等,然后卖糖果卖玩具的小贩们也推着小车来了……这个时候,广场东南角的小舞台上乐手们就开始吹拉弹唱起来了,酒吧的音乐也都响起来了,人群也开始喧闹起来。而广场西面,亚马逊剧院里的节目也快开始了。
我带着对这个久负盛名的剧院的好奇,也受了免费入场的诱惑,去听了剧院里的一场“钢琴”音乐会。一走进剧院,就感到一阵彻骨的凉意,我还真没有夸张,也并不是我这小个子中国人怕冷,剧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喊冷,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只穿了一件短袖——赤道热带雨林地区,谁会喜欢穿更多呢?!
不过这个剧院还真名不虚传,其建筑陈设的精致和富丽跟剧院外面这个城市的面貌真是两个极端。剧院大厅的穹顶有四幅很大的壁画,四幅壁画被一个大大的四角星形状的图案隔开了,四角星的中间是一个套一个的圆环直缩小至穹顶的最高点。据说这个图案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法国埃菲尔铁塔,确切地说,这四幅壁画和四角星图案就是人站在埃菲尔铁塔正下方所看到的塔身(四个塔脚和中间圆顶)和天空。(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说明这穹顶壁画是剧院建成后又加上去的;因为这个剧院1896年建成,早于埃菲尔铁塔三年)。穹顶的正中最高点挂下来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大厅的四周,有四层楼的贵宾席,贴着贵宾席廊前落下的,是大厅的22跟白色大理石柱。每根石柱在一层楼高的位置,都有一个古希腊风格的头像雕塑,这些头像所代表的都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最杰出的剧作家和音乐家,如莎士比亚、贝多芬、莫扎特、歌德等等。大厅有701个座位,都是红色的沙发椅,软软的坐垫倒给人一丝暖意;想来贵宾席的沙发可能更好。剧院的地板都是巴西最好的桃心红木做的……
音乐会还没开始,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跟我一起来的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坐在我周围的还有一对比利时老夫妇,一个荷兰人,两个日本人,一个秘鲁人,一个巴西最南部州的人……没有一个本地人,都是游客,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那两个比利时人最为这个剧院的豪华而感到惊讶,不敢相信这是19世纪末建的。他们的评论倒提醒了我一个很实在的问题,19世纪末做的吊灯,应该是点蜡烛的吧,可是那吊灯临空悬那么高,人怎么爬上去点蜡烛啊?那个跟我一起来的英国老教授(一辈子研究亚马逊地区的)就笑了,“这个剧院从一开建,用的就是电灯!”1896年啊,那个时候中国四万万同胞当中知道什么是电灯的估计也就四五人吧,连欧洲美国那时候也只在大城市里才有电灯,而广大农村小城镇地区都还没通上电哪,这亚马逊雨林正中间的一个剧院居然就有电了!
亚马逊剧院的奇迹远不止于此。这么大一座建筑的所有材料都是从欧洲直接运来的:屋顶的材料是法国Alsace来的,所有的家具和装潢都是在巴黎按路易十五时期风格做好运来的,总共198把盏水晶吊灯也是法国来的,楼梯柱子等的大理石料都是意大利来的,大楼的钢架是在英国订做的,连铺地板的巴西红木料都是送到欧洲加工后再运回来的。剧院由意大利建筑师Celestial Sacardim按照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设计,并从一开始就将电灯照明包含在建筑设计之中。剧院在1882年开工建设,1896年12月31日建成,七天后也就是1897年1月7日,举行了第一场演出。演出的是新近在意大利和美国获得巨大成功的意大利戏剧《歌女乔康达》(意大利语:La Gioconda; 英译名:The Ballad Singer),讲的是17世纪时威尼斯一名歌女的故事。
聊着聊着,音乐会就开始了。曲目单上写着的曲子都是巴赫和贝多芬的,主持人介绍我也没听清,我想当然地以为是钢琴曲。灯光亮起,我才看清舞台上的那架“钢琴”好像特别小。琴声想起,更觉得怪了,这琴声比较脆甚至有点涩,音量也小,全没有钢琴那样掷地有声。我旁边的英国老教授的儿子(十八九岁),一向鄙视巴西的破落,悄悄问他爹,“爹爹啊,这钢琴是不是没调好音啊(Oh Daddy, is this piano not tuned)?”那老教授说,“儿啊,这不是钢琴,这是Harpsichord (No son, it’s not piano; it’s harpsichord)”。我却还是不懂什么是Harpsichord,后来查了一下这玩意儿中文叫“羽管键琴”(也叫大键琴或拨弦古钢琴,葡语叫cravo)。这是古代欧洲的一种键盘乐器,主要流行于16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即巴洛克艺术时期。巴赫和(早期)贝多芬确实也做过不少羽管键琴的曲子。——这让我这个音乐盲多为难,钢琴曲都听不出啥道道来,大老远跑到亚马逊的中间还让我听古钢琴独奏。不过总体来讲,这个乐器的曲子,音都比较低,总有点悲戚甚至悲泣的感觉。(要是哪位知道那些曲子原是欢快的,那就笑笑就好了,我是真乐盲,五线谱都不识的。)
第一个曲子时,我还颇有点好奇心;第二曲未了,我早走神了,或者说好听点,思绪万千了(所以才有了这篇文章啊),还好剧院里的空调奇冷,要不然我都睡着了。直到琴师每曲终了一次又一次弯腰致谢、他那精致的燕尾服优雅地挺起裙摆时,我终于悟出点什么了:琴师他肯定不冷,他穿得厚呢。可是在这么热的地方,人人都穿短袖短裤拖鞋,他穿燕尾服扎领结,多不相称啊?就为他穿得厚,把整个大厅都搞得这么冷,多费电啊?……
许久,演出终了。当琴师的燕尾服又挺起裙摆,当大家都为这年轻的琴师起立鼓掌、并高喊“Bravo”(精彩)的时候,我忽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仿佛身处于一个多世纪之前《剧院幽灵》(原法语名:Le Fantôme de l'Opéra;英译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所描述的法国老剧院里。
听众们很多都没有即刻散去,一边兴奋地谈论着,一边掏出相机来拍照。不知道所回味的是今日演出的精彩,还是往昔辉煌的重现;说不清是在体验巴西的异国情调,还是在重修欧洲的古典文化。
出了剧院,一股热气迎面扑来。这热气一半来自热带空气的自然热度,一半来自广场上流行音乐、人群和酒杯的喧闹。这边是热闹喧天的forró音乐(一种巴西流行音乐和舞蹈风格,在亚马逊所在的巴西北部以及东北部尤其流行),那边是放着节奏欢快的桑巴音乐,远处的角落悠悠地传来Bossa Nova(巴西的另一种流行音乐风格)。剧院里出来的游客们多为此而吸引,纷纷加入了这一场又一场露天音乐会。我和我的朋友在广场东南角的小酒吧门口找到了一个桌位,这家酒吧名字就叫英文的African House(非洲之家)。这里位置不错,离广场上的露天小舞台最近,小舞台上两个歌手在唱着forró,舞台前面很多人伴着音乐放肆地跳着(不是人放肆,是这个舞蹈风格很放肆)。这两个歌手要不是拿着话筒还真看不出他们的好嗓子(或者反过来说这里多的是拿起话筒就是歌手的),音响设备听起来也算不得好,投影屏也是小小的……可是这丝毫不减唱者、听者、舞者和饮者的激情和欢乐。那个英国老教授说,虽然巴西人很爱喝酒,但是巴西没有好酒,最好的啤酒在捷克和德国,最好的葡萄酒在法国。我同意,可是当你看到普通巴西人唱得跳得喝得这么畅快,你会觉得,不是最佳的啤酒又如何呢。我们的餐点终于来了,酒吧的小伙儿端着盘子,扎着围裙,一边很熟练但还是很小心地从桌子之间窄窄的空当走来,一边不时抬眼笑眯眯地看着桌子圈外在跳舞的美女……大概他在等着下班拿了小费,就可以自己去喝酒、去和美女跳舞了吧。从别人的幸福中,我感觉到此时此间的美好。
这里的酒吧原也是有的,只不过最近几年才如此生意火爆起来,更确切地说,才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远来游客来消费。那之前怎么了呢?亚马逊剧院运作了不到20年,也就是说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整个剧院一直被弃置朽烂了将近九十年!直到2001年,亚马逊剧院才真正重新开张。这九十年间虽然偶有尝试翻新和重开,却都没有成功;以至于这豪华的剧院有一度被用作足球训练场和仓库。这段悲剧的原委还得从剧院的建成开始讲起。
19世纪末如此奢华的剧院之所以能在亚马逊雨林正中的(当时)小城建成,乃是因为当时巴西亚马逊地区正经历所谓的“橡胶繁荣期”(葡语:Ciclo de Borracha;英语:Rubber Boom)。这里的橡胶指的当然是天然橡胶。天然橡胶最初只在亚马逊雨林里的橡胶树才出产,这里的土著印第安人最早发现了它可以用做防水材料,比如给鞋子做胶底。此后欧洲殖民者就学了去,开始依样画葫芦。但是也一直没有大规模利用,因为天然橡胶对温度很敏感,热了就化、冷了就变硬。直到1839年美国人查尔斯•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发明了橡胶硫化技术(vulcanization),大大降低了天然橡胶的温度敏感性,从此橡胶的工业应用大大提升,橡胶产品也大大增加,如(实心)橡胶轮胎、橡胶水管、橡胶鞋、橡胶板材、橡胶带等等。此后,尤其是1870年之后,巴西的天然橡胶出口开始进入(小)繁荣期。1888年,旅居爱尔兰的苏格兰兽医约翰•伯德•邓洛普(John Boyd Dunlop)无意间发明了充气的橡胶轮胎。1892年,法国人米其林兄弟(Michelin)发明了可拆卸的充气橡胶轮胎,使充气橡胶轮胎的使用和维护简便易行。从此橡胶轮胎的生产进入大规模工业化,与汽车工业互为推动,在全世界飞速发展,直接导致了对天然橡胶的巨大需求。巴西一直垄断了全世界的天然橡胶出口,因为巴西之外只有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亚马逊林区有少量的产出。从1890年起,天然橡胶出口进入高峰期,占巴西全国总出口额的40%。天然橡胶的垄断出口给巴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确切地说,给在巴西的橡胶巨头们(葡语:Barons de Borracha;英语:Rubber Barons),这些巨头们也有的是直接来自欧美的大老板(,而普通的巴西割胶工人拿不到多少钱甚至吃不饱饭,橡胶巨头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在巴西历史上是有名的)。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Manaus成了整个橡胶出口产业的中心,这个产业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大部分聚集在这里(其次是位于亚马逊河河口的巴西港口城市Belém,再次是亚马逊河上游的秘鲁河港城市Iquitos)。巨额的财富马上用作了奢华的消费,Manaus成为巴西第二个通电力的城市,成为这一时期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消费市场,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奢华的亚马逊剧院、政府大楼、海关大楼和中心市场等。其中又以亚马逊剧院为这一时期巨额财富和文化追求的最佳代表。
当时的巴西虽然已经独立大半个世纪,并在1889年从帝国制改为共和国制,但是巴西总体上还是非常崇尚欧洲的贵族文化,尤其是西欧和南欧的。那些有钱的暴发户们,最典型的就是橡胶巨头们,生怕欧洲人鄙视他们没文化、在蛮荒之地谋生,所以一旦有了钱,就要大肆体现他们的正统欧式文化追求来。亚马逊剧院就是这一文化追求的集中体现。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剧院里竖起欧洲古代的剧作家音乐家雕像是蛮可以理解的,而从欧洲直接定制那么多建筑材料真是大可不必。可是,要知道当时这些橡胶暴发户们甚至用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喂马,还经常把衣服送到葡萄牙清洗熨烫再送回Manaus……在这样的社会风气里,用欧洲的建筑材料来建一个相对永久性的剧院大楼,实在已经是比较理性的文化消费了。
可是好景不长,亚马逊橡胶的黄金时期(1890-1912,葡语叫O Período Áureo da Borracha)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伟大”的大英帝国打破了巴西的天然橡胶垄断。1876年,英国橡胶专家Henry Wickham突破巴西海关的重重管制,将七万颗橡胶树种走私出了巴西,带到了伦敦。英国女王给这位大英帝国的功臣、巴西史上最大的(单人)敌人颁授了骑士勋爵。利用Henry Wickham偷回来的种子,英国人在伦敦皇家植物园培育了2800棵亚马逊橡胶树苗,然后移种英属殖民地斯里兰卡。1877年,22棵橡胶树苗从斯里兰卡移种到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植物园(新加坡当时属马来西亚),并在新加坡建立了专门的橡胶树研究繁殖中心,将橡胶树种植推广到马来西亚各地。此后,又在英属非洲殖民地试种成功。1885年前后,第一批橡胶树开始成熟并产胶(橡胶树一般需要6-8年生长才能成熟)。1910年,经过几轮的树苗繁殖和扩大种植规模,大英帝国产的天然橡胶开始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巴西的橡胶出口份额急速下跌,到1912年就已经完全失去竞争力。因为巴西的橡胶树都是自然生长的,每隔两三公里才有一棵,且因自然环境恶劣,采割成本其实很高;而英帝国的橡胶树都是大规模的集中种植园,采割成本低,生产效率高。此后在巴西也有很多巨额投资的项目来建立橡胶树种植园,但是因为亚马逊的橡胶树有一种致命的枯叶病,一旦集中种植就会大量死亡。而英帝国橡胶园在异地种植,却没有这种原产地枯叶病的细菌。于是英帝国设立重重管制防止亚马逊橡胶树的枯叶病细菌传入马来西亚——不知道是英国人管制得好,还是巴西人不够坏,这种细菌居然就一直没有传入英帝国的任何橡胶种植园。
巴西的橡胶出口一落千丈,此后仅作为国际橡胶市场的补充而已。巴西的橡胶巨头们很多就离开了Manaus,去了欧美或者去投资巴西别的地方,留下的也就坐吃山空了。Manaus从此萧条下去,整座城市居然就断电了好多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亚马逊剧院从此也就荒废了。哪怕有电,只怕也没钱请欧洲的剧团,富人们也没有心情听戏了,穷人们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兴趣。更糟糕的是,遍布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割胶工人们从此没有了生计,有的就地学起土著印第安人种木薯捕鱼谋生,有的则来到了城市,更有先前听闻“割胶致富”而赶来的外地穷人还没开始工作就失业滞留在城市了。没落的Manaus市自然无力照顾这么多被橡胶产业所抛弃的穷人。这些人就地搭了无数的简易木板房以栖身,慢慢也成了Manaus城市的一部分。只不过这样自然“发展”的城市没有什么规划,更没有什么好的市政设施,脏乱也就难免,这一城市格局至今仍然挺明显。这些割胶工人和橡胶暴发户的后代,就成了今天的Manaus人。
2001年,时任亚马逊州州长Amazonino Mendes (现任Manaus市市长;从1983至今,此人三任Manaus市市长,三任亚马逊州州长,虽然江山不倒、履历辉煌,但其实备受争议、官司缠身)决定州政府每年提供财政预算约两百万美元用于本州文化事业。作为该州文化明珠的亚马逊剧院自然受益匪浅,因而终于涅槃重生:重新装修之外,还建立了高水平的交响乐团、合唱团、芭蕾舞团;而且,剧院的绝大部分演出都免费向观众开放,少量收费演出票价也很便宜,未售出票一律免费赠送给学校学生。
不过似乎剧院的风格,一如百年前,仍以欧洲(古代)文化为正统。大厅里的莎士比亚、歌德雕塑依旧,舞台上的贝多芬羽管键琴独奏曲也依旧,琴师的燕尾服也依旧。不知道是Manaus精英阶层的文化追求一如百年前,还是他们有意保留怀旧的历史文化氛围来作为剧院和城市的特色。不过,无论怎样,这涅槃重生的剧院似乎都具有了历史文物馆的意义,每天现场演出的音乐便是活的文物,绕与梁上的,不只是余音,更有绵绵的历史。
慕名而来剧院的,没有在剧院花钱听音乐,却大大增加了剧院前广场上的兴隆。广场上的Manaus人,卖力唱歌的、开心跳舞的、酒吧服务的、摆摊卖糖的,无疑因此多了些谋生的手段,多了些快乐的机会。他们也许从不进剧院听古典音乐,因为他们更喜欢剧院外的露天流行音乐。剧院虽在眼前,但他们也许不再回想祖辈们的血汗对之的贡献;剧院既在眼前,他们大有理由好好利用剧院的存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剧院仍在眼前,而今天的Manaus人所欣赏的音乐却早已改变。不是今天的Manaus人不懂历史,而是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他们将音乐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生活延续着历史。
巴西行记之五:
巴西性事初体验
(一)
讲巴西之前,我先说一个前几天刚看到的一则新闻,说的是现在中国人在非洲越来越多,经商的、出差的、打工的。当然绝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男性,在非洲一待少则几个月多则三五年,性需求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于是有的就跟当地的姑娘好上了,也有的不小心就生下了孩子,其中又有那么几个不愿当父亲的狠心父亲拍拍屁股直接就跑回中国了,留下那非洲姑娘跟西方媒体哭诉“中国人在非洲的又一恶行”。这西方媒体怎么像苍蝇找大粪一样专找这些有关中国的阴暗面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事儿要是在巴西,很可能就不用那么狼狈不堪地逃离自己的风流债。因为在巴西,尤其是亚马逊地区(占了大半个巴西),有这样一个传说:亚马逊河里有一种淡水豚(葡文:boto;英文:dolphin;跟常见的海豚差不多),在月光明媚的夜晚,他们会上岸来,化作俊美的男子,让住在河边的少女怀孕……我听到这故事真是乐开了花,原来这经常让中国人夫妻成仇家庭破裂的风流债,在巴西可以如此浪漫地被宽容----这是什么样的天堂!
有这样宽容美好的传说,不知道是因为巴西男人实在风流,还是因为巴西女人自古多情。男人风流可能哪里都一样,我也没有兴趣多讲。女人多情我比较感兴趣,也比较有讲头,下面还是“自古”说起。话说“亚马逊”(Amazon)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传说,指的是古希腊东部有一个小国叫做“亚马逊”,其国之女人富于攻击性,骁勇善战。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者初次到达亚马逊地区,却被一队勇猛的土著女性给打败了,于是他们就把此地命名为“亚马逊”:亚马逊河、亚马逊森林等名字便是由此而来。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亚马逊女人的攻击性就(被)改变了含义,从战事转变为性事,就是说巴西女人善于对男人主动出击,或者含蓄点说就是热情豪放。巴西人把那些最富“攻击性”的女人叫做“Piranha”,piranha就是生活在亚马逊河里、人人惧怕的“食人鱼”。这种鱼其实体形不大(成年鱼20-40厘米长),但她们成群活动,一旦发现目标,比如入水的人和其他动物,几十秒钟内就可以把目标吃得只剩骨头。为什么把这样的女人叫做piranha呢,我的葡萄牙语课上有一个在巴西游历两年多的美国男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因为这样的女人属于通吃型的(葡文:“Mulher que come tudo”;英文:“woman who eats all”)。
引经据典的铺垫做了不少,下面开始说我的个人体验吧----虽说是“体验”,其实并没有“身体”的经验,不过是些经历见闻罢了。想看什么情色描写的读者,我可真是对不住了。一则因为我已心有所系,不愿沾花惹草;二则我向来行为保守,尤其在巴西人看来我几近呆傻,“露水姻缘的事情是做不来的”(一个巴西熟女对我的评价)。
(二)
去年(2007年)7月,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私立大学PUC-RIO(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o Rio de Janeiro,在巴西,私立大学都很贵,只有有钱人才读得起,好的私立大学尤其)参加短期的葡萄牙语课程,认识了一个秘鲁人,名叫Manuel(出于隐私问题,本文所有人名皆为化名),化学工程专业博士生,快毕业了。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找他问路,所以就认识了;再加上他家从祖辈起,就特别敬仰毛泽东和红色中国,因而对我这个中国人极为热情(这背后有很多故事,可另撰文说),屡屡邀请我参加他和朋友每周四晚上的“例行活动”。第一次活动去的是Lapa, 路上我就问Manuel这地方是干什么的,玩什么呢。原来Lapa是里约热内卢夜生活的中心,一整个街区都是酒吧舞厅和大排挡,他很惊讶我到了一个多礼拜了居然不知道这么有意思的地方。我说不就是喝酒吃东西跳舞嘛,他马上说:“不不不,这些不是关键,关键是在那里你可以泡妞啊!”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好地方好地方。不过,你前两天跟我说你有女朋友啊?”同去的还有一个他朋友Pedro,这时候说了:“她女朋友在巴西利亚工作,一两个月才见一次面。Manuel这个人一个星期没有女人就活不下去的。”Manuel:“我这个人很有原则的,就是跳跳舞、亲亲嘴,搂一搂、摸一摸,不上床的。一个星期一两次而已,工作累了总要放松放松啊。”我嘴上赞同,心里却想,这叫什么原则啊,标准低得几乎没有原则。Manuel见我若有不解的样子,问:“在中国,你们晚上也去跳舞嘛?”我:“也有人去的,不过不多,我几乎从没去过,我不会跳舞。那也有很多女孩子去Lapa吗?”Manuel:“当然啊,女孩子也喜欢啊,你只要跳舞跳得好,美女都喜欢跟你玩儿。”他见我表情为难的样子,马上很好心地说:“待会儿我们教你,很容易学的。”我表现地非常感激,心下却仍为难,跳舞不是我所长,更不是我所好。
等到了Lapa,几瓶啤酒下去,就开始找跳舞的地方,换了好几家舞厅,或者与其说从这个人群挤到那个人群,Manuel果然是红色阶级兄弟,很“够哥们儿”,时不时指给我看这个姑娘漂亮,那个姑娘胸大,那个姑娘臀翘。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要一直换舞厅,但是反正是在美女堆里挤来挤去,我也并不介意。后来我开始明白,他们找舞厅的标准是:第一,美女多;第二,舞厅里的人没有大群相互熟识的人,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不容易泡到女孩子,万一那群人有小混混或黑社会性质的,就会有麻烦;第三,舞厅不需要门票或者门票很便宜。至于舞厅里酒水贵不贵是无所谓的,因为大不了出去再喝。Manuel跳舞跳得不错,泡妞更是不遗余力,舞步总是冲着美女移过去、然后贴上去,不需要只言片语,两个人就可以开始优美地配合……没有美女在跳舞的时候,就去邀请在旁边歇着或看着的。Pedro跳得也很不错,而且转眼间,已经和一个美女步出舞厅,在街角搂在一起亲嘴亲了好久,只遗憾那美女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早早地(凌晨1:30)离去了,不能陪他整个晚上。Pedro之前表现得比Manuel要斯文得多,没想到泡妞的本事一点不比他差,在那天晚上显然比Manuel更成功。他们俩见我一直只在旁边站着喝水,没有任何斩获,决定助我一臂之力。不久来了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看起来是亚裔。Manuel说:“这三个女的怎么样,跟我们三个正好呀。那个亚裔比较漂亮,待会就是你的了。”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已经上去邀请她们了。他在舞厅的另一边跟她们指手画脚地谈着,时不时指着我和Pedro;因为音乐声音很大,我根本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是说了很久之后,居然没有成功,他们都很失望,我却松了一口气。再过了一会儿,Pedro和我都想回去了,Manuel却意犹未尽。回去的路上才知,原来Pedro也是有朋友的,就在里约热内卢,再过几个月就要结婚了。我又是一阵惊讶,原来女朋友是否在外地根本无所谓,每周四晚上的例行“鬼混”,是他们女朋友允许之下。我心想他们的女朋友是不是也有每周一次的“鬼混”,却没好意思问。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我一个研究巴西Funky音乐的朋友带我去一家舞厅,这家舞厅的Funky乐师(DJ)在里约热内卢是数一数二的。那天晚上的舞会是不对外的,只有被邀请的人才可以进去。因为朋友的关系,我的名字第一次上了VIP名单。Funky音乐简单地说,就是乐师对原有其它音乐进行现场的再发挥,用电子设备把其中一些音节调高、调低、重复、扭曲、拼接,在我听来就是很响很吵很奇怪,第一次还有点新鲜感,第二次是再不会去的了。Funky音乐里跳的舞在我看来也就是乱跳,没有什么套路步伐可讲,只要节奏大致对得上就好了,因为此,所以我倒是也乱跳了一会儿。其间,就跟一哥们开始聊开了。他是Funky音乐新入门的乐师,来这里观摩今晚的大师。没聊几句,话题就自然地转向了女人,他得知我一个人在里约热内卢这么多美女的地方,“居然(!!!)”没有泡个妞,就很热心地要帮我找一个。我说不必了,我有女朋友的,在美国。他极为惊讶地说:“在美国?!兄弟啊,十万八千里的,她哪里会知道啊?!”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中国女人比较爱吃醋。”他笑笑:“哪里的女人都爱吃醋。”言下之意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就开始品评舞厅的女孩子,就像Manuel上次给我指点的那样,这个脸蛋好,那个身材好……在那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我们一手拿着啤酒,一边踩着舞步,一边大声地谈论着舞厅里的女人,我忽然觉得我开始理解巴西人的一种生活态度:音乐、跳舞、啤酒和异性,那样自然和轻松地融合在一起,都成为快乐的来源;不像我们中国文化中把性作为一个很特殊的范畴单独隔离出来,加上沉重的道德束缚和压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Manuel和Pedro的例行“鬼混”,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工作累了“放松放松”跟朋友吃饭唱卡拉OK,其性质便是一样的。后来我又拜访了Mauro的住处,他跟两个同学合租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他两个室友因为女朋友在,一个住了一间卧室,一个住了客厅(用布帘隔开了过道),Mauro住在楼梯口用木板隔出来的只够放一张单人床的空间里。他室友告诉我,Mauro隔三差五带女孩子回来过夜,我有点惊讶,不是因为他有女朋友还频频“出轨”,是因为那些女孩子竟然也不介意这么寒碜的“卧室”,两个人在床上换个姿势都不容易,更不用说发出任何声音室友都会听到。想来性爱对于他们是真正的人之常情,至少不会像对于中国人那样是很敏感、甚至羞耻的事情。
(三)
2009年8月和9月,我主要在巴西的亚马逊州。到亚马逊州的首府Manaus的第三天晚上,我就有了更为刺激的经历:一次不太艳的艳遇。
我在宾馆认识了一个人Daniel,他的好朋友Roberto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当时正要找整个研究所的人做访谈调查,而且他们俩正好约了那天晚上在我们宾馆附近的一家酒吧喝酒。天赐良机啊,我也去。到酒吧还没几分钟,同在宾馆的另外三个人也来了这酒吧,于是就一起坐着喝酒聊天。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土耳其裔的英国人,说着一口比本土伦敦人口音还重的伦敦音,刚19岁,在巴西旅游,什么正事儿也没有,整天就想着怎么泡妞上床,他一天到晚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兄啊,我他妈真想肏一个巴西女孩儿(Oh man, I really want to fuck a Brazilian girl)!”(原谅我的用词,只因这哥们儿原话如此)他已经在这个宾馆住了三个多星期,还没有把巴西女孩搞上床过;每次走在大街上,他一看到稍微漂亮的女人,就要一边狰狞着脸,做着双手抓女人胸部的动作:“你看看那肉肉(Look at that body)!”或者“你看大奶子”或者“你看那屁股”……所以我相信,他是真的极度性饥渴,因为不会说葡萄牙语的关系,至今未能得手。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女的,20出头的样子,巴西南部来的,皮肤很白,高高大大,成天穿着布料很少的裙子在宾馆里走来走去,却不大说话。另一个男的,也是巴西人,20几岁,骑摩托车环游南美洲,已经骑了5万公里,是当年切•格瓦拉的两倍多了,人很健淡,样子也不错。啤酒喝了没几圈,这南部美女和摩托仔就走掉了,过了个把小时的样子只见远远地正往回走(我们的桌子在酒吧门口人行道上)。大家一对眼色就明白了,他们俩刚才搞过了,我却不大明白,Daniel就给我解释说他们俩刚才或者做爱了或者至少亲嘴爱抚了,然后Roberto耸耸肩:“正常(葡文:Vou facil;英文:I am fine (with anything))。”
然后那土耳其哥们儿坐不住了,开始行动起来,并最终把我也拖入了一场极为尴尬的不艳之艳遇。我们邻桌的邻桌坐着一个女的,一个人喝着啤酒抽着烟,长相一般,胸部挤得比较挺。土耳其哥们儿拿着啤酒就过去了,过了十几分钟就回来了,原来是语言不通,两个人互相搞不清对方的意思。于是乐于助人的Daniel就去给他当翻译了。泡妞这事儿还夹个翻译,本来就挺奇怪的了;更高效的是,他们俩三分钟就回来了,原来那女的是个暗娼,跟那土耳其哥们儿开价300块(巴西货币,大致相当于US$200),看他们要走,还说可以打折到250块。那土耳其哥们儿白兴奋了一场,很郁闷,Daniel说那个妓女因为对外国人所以开价高,本地人最多100左右肯定搞定,那哥们儿更是羞愤地不知想砸桌子还是砸自己。正在这个时候,邻桌来了四女一男!那哥们儿又跃跃欲试,又怕语言不通、不敢轻易上前。此时Daniel的女朋友正在来酒吧的路上,他说他不能再帮忙了,他女朋友很爱吃醋,要是看到他正在跟陌生女人讲话,他今天晚上就光道歉都不够了(上床的机会就泡汤了)。而那对巴西临时鸳鸯已经离开,所以Roberto就出手相助了,他们俩就在那桌聊开了,而Daniel的女朋友到了,但是两个人一转眼就不见了。于是我们这桌只剩我一个人,邻桌的女孩子叫我也过去她们那桌,我好像实在没有理由一个人坐着,只好过去了,想来不就是聊聊天喝喝啤酒,没什么大不了。
刚开始是大家一起聊天,后来就很明显基本上是一男一女对聊了:本来就在这桌的一个男的和其中一个女的,两人号称“普通朋友”而已;土耳其哥们儿和这四个当中年龄最小也最漂亮的那个;Roberto和一个看起来年龄最大(40左右)也最不漂亮的女人;我和一个看起来是第二老(35岁上下)第二不漂亮的女人。(不过,巴西女人、尤其是亚马逊州的女人在我看来总是显老10岁左右,所以这两个女人真的比较年轻也是很有可能的。)过不多久,Roberto和他的女伴就开始搂着亲嘴了,亲个五六分钟十来分钟才放开喝口酒然后继续。我原以为我也是能够耸耸肩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的,可是他挺帅一小伙儿,学历高职业好,居然这么快就跟这样一个女人%$¥#—@*+,我还是觉得这两个人实在有点不搭调,而且就在座位上,大庭广众,众目睽睽。很快,本来就在这桌的那对“普通男女朋友”也开始抱着亲嘴了。那个小美女却一直不肯跟土耳其哥们儿亲嘴,再加上交流困难,他们俩都急了,我就开始给他们翻译,原来那土耳其哥们儿一上来就表达了晚上想过夜的意思,那小美女不肯,说“我们不是这样的女人”,于是也不肯跟他亲嘴,怕他乱来。搞清楚之后,旁人就开始起哄了,“亲就亲吧,没事儿”,那土耳其哥们儿在近两个多小时的软磨硬泡和旁人的怂恿之下,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搂上了那小美女亲嘴了。
我和我旁边那个女人还是一直在聊天,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了这气氛颇有些尴尬。果然,那小美女亲了一会儿之后,三个女人都在问我和我的女伴怎么还是坐着瞎聊没有实际行动啊,本来就在这桌的那个男的尤其怂恿的厉害,还时不时地用他初学的英文跟我说:“她喜欢你。快亲她吧。她很想你亲她 (She likes you. Kiss her. She wants you to kiss her)。”我明白啊,可是我不想啊!那个女的一会儿抓过我的手问我会不会看手相,一会儿故意挠我痒痒拧我腰,一会儿说我嘴唇真性感,一会儿说我睫毛真漂亮,后来她甚至很轻很快地跟另一个女孩说:“我们一直就在聊些很无聊的话题”……她以为我听不懂的,其实我听懂了,我有点因为我的无聊而感到歉意。因为之前她跟我说她们是附近一个医科学校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去夜校学习,因为又工作又学习很忙很累,每天只睡4-5个小时,今天下了课之后来酒吧玩一玩放松放松的。可是却偏偏碰到了我这个“木头”。我装作我葡萄牙语很不好,对她的语言和行为的挑逗都装做不懂,以减轻直接拒绝亲嘴的尴尬。后来我又觉得,她会不会以为我觉得她难看才不愿意,这样她岂不是自尊心受打击,并且在朋友面前没面子,于是我干脆告诉她,我们中国人陌生男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是不可能亲嘴的,中国年轻男女往往要语言交流几个月之后,才会开始亲嘴,又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上床,而一旦男女朋友关系固定或者结婚之后,就不能跟别的女人亲嘴上床了,这是我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化。她说她理解,“可是现在你在巴西啊,应该入乡随俗嘛,你不是说你在学习巴西的语言和文化吗?”是啊,我还真无言以对了,只好继续装傻,我说我这个人脑子不大灵光,做什么事情都慢,吃饭慢,喝酒慢,学葡萄牙语学了三年还结巴,至于和女孩子交往,我也得慢慢学慢慢适应,也许下次我们再见面吧。她倒较起真来了,要把她的电话号码留给我,我说我没有电话,她就要我的电子邮件地址。顿了一会儿,她又很怅然地说:“其实你过一会儿就会把(写着我电话号码的)那张纸条扔掉,对不对?”那一刻,我真的羞到无地自容,我觉得我什么坏事、哪怕出格一点的事都没有做,可是那一刻,我好像是被扒光了衣服站在她面前,无遮无挡又无处可逃。这极端的尴尬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凌晨一点半左右,我们终于离开了那酒吧。我好像犯了错误似的,道别的时候,连巴西人日常的亲面颊礼也没有做,只是说了一句,我会留着你的号码的,就仓惶而逃。
走回宾馆的路上,只有我和那个土耳其哥们儿,他一边走,一边用英语大声地骂着,“靠,还是没能把那小妞搞上床!靠,我他妈花了两个小时她才让我亲!你说她是不是根本就不喜欢我?你说要是我刚开始先不说想跟她做爱,只是亲嘴然后再循序渐进,会不会反而更有机会?”我一边在为结束刚才的尴尬而松了一口气,一边又为那个女人感到一点歉疚,百感交集之时,这哥们儿居然还问我这样这样技术性的问题,我真想说“你丫给我闭嘴!”——我的巴西朋友早就警告过我,“深更半夜在巴西的街上讲外语是很容易遭抢劫的!”
(四)
过了几天,我就去了亚马逊森林深处的一个森林保护区做调查。在森林里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其他五个人一起蜻蜓点水似的参观了好几个村庄:两个英国人(父子),一个德国哥们儿,一个法国哥们儿和一个巴西美女;除了那个英国父亲,我们五个人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虽然走马观花一样,但多少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这里的女人都有很多的孩子,少则四五个,多则八九个。我们看当地人的生活水准都挺低的,小孩儿的受教育条件也不好,就问那位巴西美女当地人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少生点,比如用避孕套。这位巴西美女(我一直说她美女是因为她真的很漂亮)是圣保罗人,但是在这里做森林保护和二氧化碳减排的项目已经很长时间,对当地人很了解。她说她还真地问过当地人这个问题,他们回答说:“喜欢直接做,带套不爽(葡语:gosta de pelado;英文:like/prefer sex with naked [dick])”。回答得还真够实在的。此外,还有很多年纪不大的女孩儿(小至14岁)已经怀孕生小孩儿了,没有丈夫,都是跟父母住着的,当地人也习以为常(后来又了解到,在城里,包括首府Manaus,也是如此),看来那个淡水豚上岸让少女怀孕的传说还真的是很有民间基础的。(在整个亚马逊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建在河岸上的,因为河运是主要甚至唯一的交通方式,大则轮船,小则独木舟。)
我想起前几天在酒吧的经历,年轻人轻易地进行性接触,做爱又不喜欢带套,早孕也是自然的了。可问题是,农村里没有酒吧,这里的村子都很小(每村10户左右),甚至连小店都没有,那主要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开始(性)接触的呢?那巴西美女告诉我,聚会(葡文:festa;英文:party)是一个主要的机会,这里的人们经常有聚会,一个村子有聚会,附近好几个村子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去。巴西人喜欢聚会就像喜欢足球一样,真是全民参与,聚会(和足球)根本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村人同样热衷于此。可是我又纳闷儿了,农村里没有酒吧舞厅,没有那么多音乐设备,甚至连电都每天只在晚上开两三小时(汽油发电机),怎么搞聚会的呢?也跳舞么?原来他们对跳舞,主要是Forro,的热情一点不比城里人差,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美丑人人都跳。
Forro是巴西一种很流行的音乐风格,与之相伴的舞蹈样式也叫做Forro,在巴西的北部(包括亚马逊地区)和东北部尤为流行。主要的乐器是手风琴和吉他,曲调快慢适中,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巴西咖啡的味道,很甜很腻、浓情蜜意。Forro舞蹈是一男一女搭配跳的,我在宾馆认识的一个奥地利姑娘(在巴西游历多年)对Forro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就是把你的右大腿塞到你舞伴的两个大腿之间,或者说互相夹住对方的右大腿,然后肚贴肚、胸贴胸、脸贴脸地互相磨啊蹭啊——这根本不是跳舞,这是赤裸裸的性挑逗!”她不喜欢跳这个舞,所以说得稍微夸张了点,其实也不止这么简单,每过一会儿男的要把女的甩出去、转过圈、然后猛地拉回来,大腿和大腿、胸和胸结实地撞一下,然后继续磨啊蹭啊……不过据我仔细观察,真正能够做到既夹着大腿,又贴肚、贴胸且贴脸跳舞,其实难度是很高的,有的巴西人真的贴这么紧还能把Forro舞跳得那么洒脱奔放,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也有的人显然跳得不好,却也贴得这么紧,这种情况纯属吃豆腐,至于谁吃谁还是互吃我就搞不清了。
回过头来说这亚马逊农村的聚会,当地人告诉我们,那个周六晚上,邻村(快艇20分钟、独木舟一小时)正好就有一个聚会,邀请我们这些人全都参加。我们都很想见识见识这亚马逊森林深处的农村聚会是什么样的,可惜后来我们全都没有去,那四个欧洲人是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离开了,怕赶不上船。我是要留下来继续待两个星期的,没有时间上的顾虑,他们都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我听说了这次聚会是因为一个节日,这节日是关于Nossa Senhora de Conceção(英文:Our Madam of Conception/Pregnancy;中文:助孕圣母/送子观音),我怕被村里的女孩子给要求“助孕”,再加上这样的舞蹈……差点没把他们笑死。我说我点儿惊弓之鸟了,上次在城里的酒吧差点被人强迫接吻,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相对比较保守,陌生男女头一次见面就接吻做爱的事儿,我做不了,因为我一时很难改变我已接受的文化。他们倒也觉得有道理,尤其那巴西美女连说:“你应该坚持自己的(中国)文化,这很好!”我听得出,她是见多了外国男人到了巴西就四处流情或与其说留种。然后大家开始讨论起来各国男女交往的方式,在巴西,从认识到接吻只是一小步,从接吻到做爱往往是一大步。在西欧,尤其是在法国,从认识到做爱是一小步,但是接吻却不大容易,那里的人觉得接吻是要有感情基础的,而做爱可以完全是为了性的享乐。然后我说在中国,从认识到接吻是很大的一步,从接吻到做爱是更大的一步,总之每进一步都不容易。那位巴西美女又补充说,在巴西,聚会之中或之后,有人直接开始做爱也是正常的,不过这“正常”并不是说经常会发生,而只不过发生了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罢了。那看来我真的是过于紧张了,反而错过了一次了解巴西老百姓生活文化的很好的机会。
这里可以补充一点的事,鉴于亚马逊州偏远地区教育资源匮乏,这个森林保护项目从国际二氧化碳市场获得的资金,部分用于在保护区内开办学校,相当于普通的中学,但是加入了更多关于森林保护的知识,来学习的学生都是附近村子15-25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学校提供免费的食宿。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是,学校正式开课才3个月,总共不到60名学生,已经有3个女生怀孕了。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和那个巴西美女,还有一个学校的工作人员,正在一边擦洗学校的太阳能电板。他们说,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学校要养小孩,而且那些年轻妈妈也很难专心学习。我在赤道的烈日当空之下爬着梯子擦洗着太阳能电板,忽然就想起来这些学生怎么不多干活呢,学校还要请人给他们做饭、维护太阳能电板等各种设施,于是就建议那巴西美女,以后学校得让学生多干活,那些学生工作时间多了,谈情说爱,哦不对,谈情做爱的时间也就少了。他们笑得要从梯子上掉下来,都说我的建议很好——这是迄今为止我对这个森林保护和社区发展项目的最有建设性的贡献。
离开亚马逊林区农村回州府Manaus城的头天晚上,我在县城的一家宾馆里住,同住的还有在基金会工作的两个男的:一个45岁的老兄Marcelo,秃顶,一双大招风耳,他负责各个森林保护区的物资供应和基建工程,爱开色情玩笑,然后自己笑得最猛;另一个是跟我同年的德国裔巴西人Adu,瘦骨嶙峋,很乐于助人又很文静,总是面带微笑,露出一副夸张的牙套。那天晚上县城里可能是最好的一家俱乐部有聚会,主要是县城里的小青年,聚会内容当然就是啤酒、声音震天的音乐和粘在一起的Forro舞——我总在想巴西人三天两头有这种聚会,凌晨四五点才散,那些邻居是怎么睡觉的。在舞场,我们遇见了宾馆的一个女服务员和宾馆隔壁小店的老板娘(应该都在30岁以下)——白天看不出来,晚上打扮一下,穿上布料很少的晚礼服,没想到也挺好看的。两个女的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因为我夸她们漂亮,她们也相继来教我跳舞,不过我能感觉到她们跟我跳显然不够尽兴,我只用手挽着她们的腰,其他哪都没贴着,因为我想低头看对方的脚步来学习,不过我一低头先看到的总是那大半露在外面的胸部,真是让我不知道看那里好。出乎意料的是,本来很文静的Adu原来是跳舞高手,就是把四个部位都贴紧还能跳得很洒脱奔放的那种境界,两个女人轮流跟他跳舞,本来说好要跟我早点回去的免得误了第二天早上的船,结果却跳到3点多才走。来聚会之前,在宾馆房间里,Marcelo拿着一打安全套甩来甩去,说今晚要吊个女人回宾馆做爱的;可是在聚会上,他却没有找到一个女人跟他跳舞,于是很失望的他早早地就拉我一起走了。刚出舞厅,直接拉过路边的一个小姑娘,说了几句话,就跟我说搞定了,那小姑娘过会儿来我们宾馆,还说把我房间号码也告诉她了,他那边完事后就让那姑娘来敲我的门。这老兄还真是直爽,助人为乐事先问都不问,我赶紧说不必了,我很累了,想早点睡觉免得耽误了第二天早上的船。第二天在回Manaus的船上,Marcelo一会儿跟我说昨天晚上的姑娘不错,很爽;一会儿又拿出手机给我看他老婆和儿子的照片——第二天就要见到老婆了,头天晚上还特地要招妓,生活真是很有情趣。有意思的是,他儿子才两岁,居然也长了一对招风大耳,我脱口而出,你儿子长得跟你很像啊。没想到他倒认真了,说:“感谢天主保佑啊,你说呢?(葡文:Graça a Deus, né;英文:Thank God,right?)”我赶紧说,是啊是啊,心里直想补充说,“就你这情况,还真是不容易的”。
(五)
回到Manaus城后,原计划只在城里待一个星期,因为一些变故,直待了近三个星期。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就会觉得无聊,尤其是在Manaus这个我见过的最脏最破最无趣的大城市。Manaus位于整个亚马逊大森林的正中间,亚马逊河的岸上,不通公路和铁路,交通运输全靠飞机和轮船,因而虽然是有着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是城市发展市政建设却不大好。若不是因为工作,我是不愿待这么久的。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尤其是男人,是喜欢这座城市的。
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男子,肤色较浅(在Manaus不多,而且往往属于中上阶层),穿得干净整洁(这里的人都是拖鞋短裤短袖为主),还会说两句口头英语,我以为是个很正经的人。没想到刚说了几句,就开始聊起了女人,“在Manaus感觉怎么样?喜欢这地方吗?”在人家的地头上,我能说不好么,“好啊,不错,我很喜欢。”他马上开始笑嘻嘻地说:“很多漂亮女人,对吧?”嗨,他原来指的是这个啊,我也笑嘻嘻地随即附和:“是啊是啊。”他见我也好这口儿,就说开了:“我跟你说,巴西美女多,但是Manaus这个地方尤其多。人口统计数据说,Manaus的女人比男人多两倍还不止,再加上还有很多Gay(男同性恋),所以在各种聚会上,经常一个男人对五个女人甚至20个女人都有可能。”我瞪大了眼睛:“我靠,这里真是男人的天堂啊!我以前还真没听说呢。”他说:“现在知道了吧,你算来对地方了。”他接着说他老家是亚马逊州的一个内地小城,很早就来了,“在这个地方定居生活很不错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看着车窗外破烂的街道和车前面拥堵的车流,我完全明白是什么让他如此钟爱这个城市。他又问我结婚了没,我说还没呢——我其实已经订婚,但是故意这样说,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下面的谈话会更有意思。他接着问:“想找个巴西女人吗?”我说:“想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在中国,男人要娶妻子得有钱,买房子、办婚礼等等,还得有个好工作,要不然女人不肯嫁。不知道巴西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他说:“巴西女人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只要长得好看点(葡文:bonito;英文:beautiful),对上眼了,就结婚了,你住城里一个小破房间,她也跟你了。”我很高兴:“那巴西女人好多了,中国女人想法多、要求多。”他补充说:“也有的女人看钱的,尤其是那些很漂亮的女人,没有钱很难搞到的。不过总体来讲,巴西女人还是比较容易(葡文:facil;英文:easy)。美国女人怎么样?容易吗?”我有点不好回答:“我没有实际试过,总体来讲,可能介于中国女人和巴西女人之间吧。”他附和说:“还是巴西女人比较容易,不错”——一副美滋滋的表情。我们又聊起他已经结婚,妻子是小学老师,有一子一女。我问他,还有别的女人吗?他转过头来笑笑说:“没有了没有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年纪可有多着呢,两个三个那是很正常的,四个五个也有过。现在我已经45岁了,有一个老婆就够了。”我开玩笑似的问他:“真的假的(葡文:serio; 英文:seriously)?”他说,“真的”,不过我并不相信,一方面是因为此前聊天时他表现出的兴(性)致不减当年,另一方面是在Manaus,这样的男人可不少,上面说的Marcelo便是一例,警察Raul也是个很有趣的例子。
在Manaus一个周五傍晚,我去亚马逊州环保局等人有事情,我在环保局的内部餐厅兼酒吧要了一杯果汁坐着等,这酒吧的老板娘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母亲,之前就认识了。过不多久,只见乐队和成箱的啤酒就来了,原来是晚上6点有生日聚会。来参加聚会的人主要是环保局的小公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如清洁工和专驻环保局的警察。到近7点钟我朋友也没来,我就打算走了,问之前打过招呼的两个警察怎么坐公车,他们说不知道但是7点半他们也就走了,开车送我到公车站,那我就再等半小时吧。我问其中一个警察Raul结婚没,他说早就结婚了,15个孩子,最大的26岁,最小的……他想了想说,四岁或者五岁。15个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怪怪地说,生了不少了。没想到Raul倒也不介意我说他孩子多,他一边用右手拳头打着左手掌心(这里通用的表示做爱的手势),一边感慨对我说:“停不住啊,兄弟!”顿了顿又说:“不过我老婆说了,不能再生了。嗨!”我不知道他感叹的是孩子多,还是以后性生活要少了。他的警察同事说,Raul特别喜欢做爱,Raul就一个劲儿地笑,毫不否认却一脸自豪,我挺佩服他的境界:这世上,有人爱喝酒,有人爱足球,他独爱性事,也爱得坦坦荡荡,不都是人生在世的乐趣嘛。
这时候环保局的两个中年女清洁工加入了我们这一桌,他们四个人显然早就熟得很了,我在旁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几罐啤酒啤酒之后,其中一个警察Raul就开始调戏其中一个相对年轻好看(只是相对来讲,其实还是很难看)一点的女清洁工Josefina。那Josefina毫不生气,只是咯咯直笑,我也没有听清他们说的每句话。忽然Josefina转过来对我说,Raul说要找我今晚去motel。我想多半是Raul有非分之想了,以免唐突,我装傻地问,去motel干什么呢?Josefina朗笑三声,“motel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啊?!”然后稍微压低声音说,“做爱啊,Raul那家伙想跟我今晚做爱。”我很好奇地问,那你去吗?她直摆手,我问为什么不去啊?她有点腼腆地说:“做爱这事情要有感觉的。我跟他同事,这么熟了,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不去的。”随后Raul和Josefina开始关心其我来,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旅行,多久了,和巴西女人相好过没有?我说快一个本月了吧,没有相好过。他们很惊讶,一个半月,一个人?!Josefina顿了顿,问我,那难道你就没有欲望么?你看到漂亮的巴西女人就没有做爱的想法么?我可不希望被人误以为是同性恋,我马上说,我当然有欲望啊,也想做爱啊,可是我工作忙,而且还没学会怎么和巴西女人交往,比如她们喜欢些什么,吃饭、喝酒、跳舞还是送礼物,等等。
与此同时,另一个警察Romero和女清洁工Socorro一直在跳Forro,跳了一曲又一曲,很投入的样子,直到快八点钟,那女的说,她必须得走了,她丈夫今天晚上出差去外地,她必须赶回去道别。Romero自然不肯让她走,和她并肩坐着,他一只手抓着Socorro的手,一只手抓着她的肩膀,说着悄悄话——丈夫要出差了在家等着,妻子还能和别的男人这样缠缠绵绵,真是让我这没见过世面的人啧啧称奇。
我看过的(不多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中,关于情爱的主题,所涉及的不是古代的王孙小姐,就是现代的城市白领,让我觉得普通中下层男女的感情和性事却很少被书写。我第一次这么直接地感受到,小老百姓的感情和性事其实也很值得书写,甚至别有情趣,如Raul的率性坦荡,如Josefina感性和真诚,如Socorro和Romero的缠绵悱恻。
(六)
写到这里,我有必要说明一下,虽然我觉得于性事一端,巴西人比中国人要率性随便一些,但是不要因此而根据我们中国人相对保守的性文化,而简单地对巴西人做负面的道德审判,如放荡或道德堕落之类的。每一个民族和文化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道德标准,用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标准去判断别人,很容易,却往往没有正面意义甚至带来民族文化间的冲突。
就像前面讲到的,如果视性事为快乐而较为自由,便是放荡堕落,那么巴西人轻易接吻而法国人轻易做爱,到底谁更放荡和堕落呢?以前的中国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合法合理地三妻四妾,而这些妻妾们去没有任何的性自由,更别说因为富人三妻四妾而间接剥夺了贫穷男子的性权力。现在的中国社会,虽然重婚是非法的,但是有钱有权的男人养情人、包二奶也屡见不鲜,更别说出入烟花柳巷、到处采花偷蜜;女人们或被迫或主动地成为这些男人性自由之下的情人和猎物,而贫穷的男人仍然为娶妻而犯愁。那在中国社会中,大众的性保守甚至于性权力被剥夺,和少部分男人因为钱和权却具有较大的性自由甚至剥夺他人的性自由,这种现实难道就是道德的?我觉得至少是不公平的,对那些被剥夺了性权力的弱势女人和男人而言,这甚至是不人道的。而相对地,在巴西社会,虽然有钱有权的人当然也可以金屋藏娇,也更容易找到漂亮的女人(或男人),但至少普通民众因为社会文化的宽容,也具有一定的性自由。如果我们认同公平(正义)或民主是每个社会值得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在性事一端,巴西人拥有比中国人更多的性公平(或民主)。
巴西人对性的宽容不仅体现在民俗传说和社会文化中,甚至囊括于法律体系中。巴西的法律规定,夫妻感情不和可以申请“合法分居”,合法分居并不是离婚,不涉及家庭财产和子女养护这些法律问题,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夫妻双方都可以各找异性同居,这期间的同居不可以成为夫妻一方指责另一方应承担离婚之法律和经济责任的理由。当然,同居之后,如果夫妻双方和好,自然婚姻继续。想想在中国和美国,离婚不仅在感情上,更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是一大挑战,光繁琐的法律和行政程序有时候就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在此期间的性生活怎么办?或者,如此折腾实现离婚之后,又想复婚了,岂不又是一番折腾,直折腾到敢情好进、性欲冷却。所以回过头来看巴西法律中特设的合法同居阶段,那实在对包括性需求在内的一个极为人性的设计。
巴西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和巴西中下层民众谋生之困难是众人皆知的,但是巴西社会能够在文化和法律上开出一扇窗口来宽容和鼓励性的快乐,实在也是值得赞赏的,往小了说,有利于改善个人生活快乐指数,往大了说,有利于社会稳定啊。
我尊重和欣赏这世界上多样的文化,包括性文化,却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作为个体和整体,就应该“拿来主义”、直接学习。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是在其历史上形成的,并适应其民族其地方的生活的。我可以通过中国和巴西社会的历史很简单解释一下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总是强调夫妻的忠贞,尤其是女性的贞节,这是有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基础的。我们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前就差不多形成了延续至二十世纪的农耕文化,在农耕文化中,土地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而偏偏中国可耕地有限,人口却不少,因为人口压力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威胁,中国人的可耕地拓展到了唐代就基本上到了极限(到达了广东、海南和台湾)。那么在人口和土地压力紧张的情况下,要保障家庭和宗族对土地的所有权,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是严格的财产(主要是土地)继承权。而要保障这严格的(父系)继承制度,不是财产流于外人(其他家族),就要保证继承财产的是男人的亲生儿子,换句话说,严格保证女性的贞节。因此说,一个社会的性道德乃是维护其政治经济制度稳定的重要保障。今天的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即将解体,在功能上作为这一文明的保障制度的性道德也肯定会发生变化。至于什么变化,我也说不清。不过我敢肯定的是,道德作为一个文化的基础,是有其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强调性忠诚的道德意识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在很长的时间之后,才会积累成大的变化。
巴西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自然是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其中有约束性自由的因素,如天主教即认为通奸乃是一大罪,也有对性自由的间接鼓励,如欧洲王室贵族名流中的情人文化及其在社会整体的示范效应。而巴西的殖民地宗主国葡萄牙(以及西班牙)在十一、十二世纪时曾遭到发源于中亚的莫卧儿帝国的占领,因而对异族间的性行为和通婚有相对的宽容。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后来巴西社会文化的形成。而从巴西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看,巴西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甚至一定成程度上直到今天,有一个基础性的要素就是地大物博。每个人只要稍有勇气,就可以在广袤的“无主”(其实有些是有土著印第安人居住的)土地上开辟一片自己的家园。是不是能够从父亲那里继承财产和土地并非那么重要(甚至在巴西刀耕火种为主的生产方式之下,一块土地连续使用10-20年之后便失去肥力了),带上一把镰刀,驾着一个独木舟往亚马逊河以及其他无数河流的上游几公里甚至几百米就会有未开发的森林和土地。做父亲的也不用在乎儿子是否亲生,也不用在乎是否多得养不起,因为反正有无尽的土地让他们自己谋生去。而对夫妻忠诚的(相对)有限强调,更多的是基于感情(和一点宗教道德约束),而对于性本身——作为快乐的一个载体——是没有很强的政治经济约束的,有的是更多的宽容。而与中国的情况类似,刀耕火种的迁徙式农业日渐失去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大农场农业和城市工业日渐成为中心,上述的性文化也面临着问题。去年很长一段时间,巴西新闻的一个主要话题便是一个富翁去世后的财产继承问题。这个富翁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清楚自己到底多少钱,二是搞不清自己到底多少个情人,更搞不清自己留下了多少的种子。等到他死后,一个、两个、三个……十来个情人,二十几个子女浮出水面,要继承他的财产,这些女人和孩子们,从床第之间争到法院,从法院争到媒体,直到举国舆论的焦点为之转移。我想平常总是被骂的那些腐败、不作为的政客们那段时间肯定是猛松了一口气——瞧,巴西的性文化又一次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作了一次贡献。
好像扯远了,我说这些主要是想表明一个社会的性道德和文化是有其政治经济历史基础的,无论是作为社会整体还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人,都很难轻易地改变。不明就里地简单照搬,要么是邯郸学步、弄巧成拙、贻笑大方,就好像日本人曾热衷于让其女性与中国宋代男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种男性做爱来改良日本人种、提升文明水准一样;要么是别有用心——为自己的(依据自身文化标准的)道德堕落寻找漂亮的借口,就好像如果我这个在保守的性文化中长大的中国人来到巴西之后只为一时欢娱就四处留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