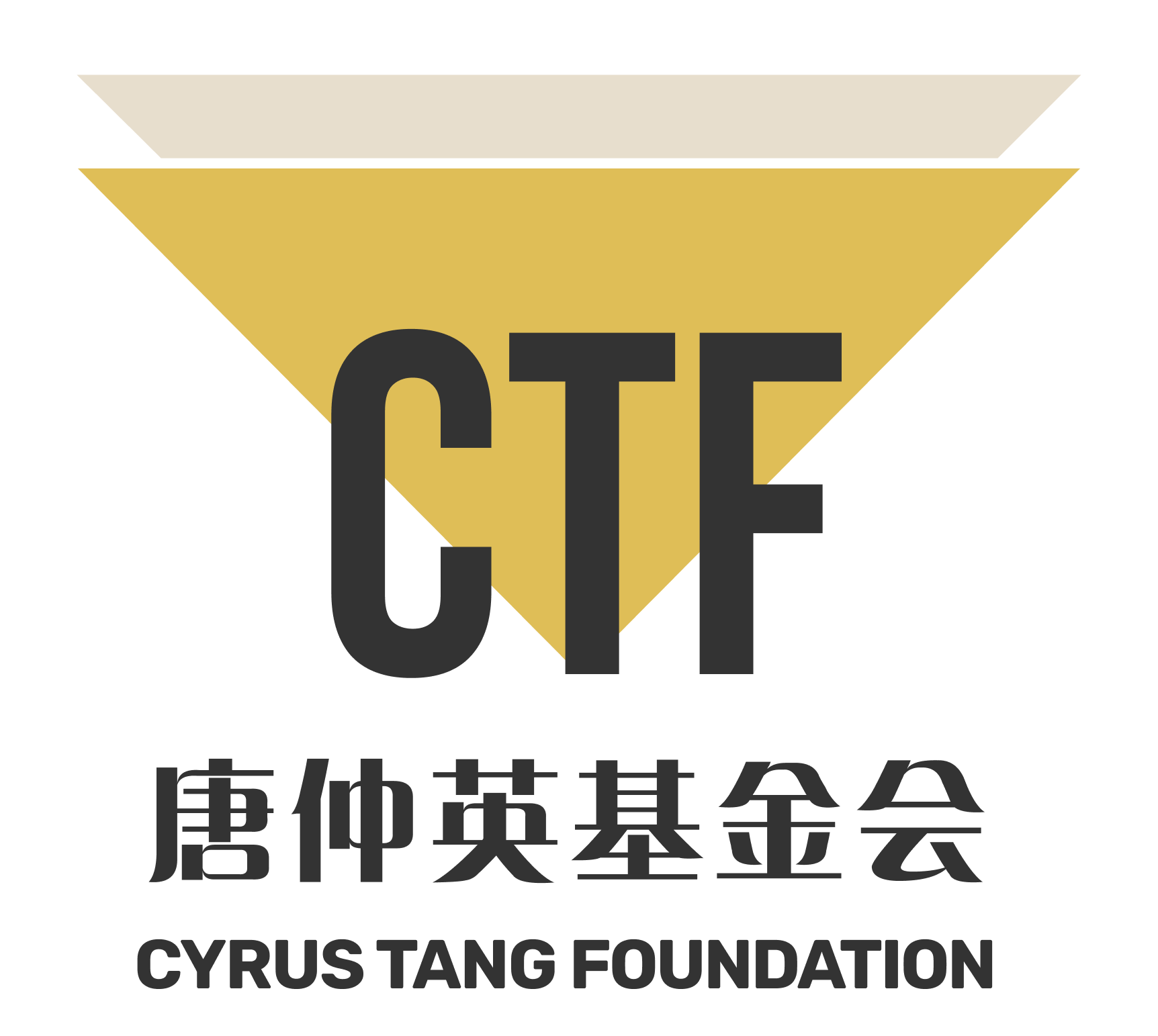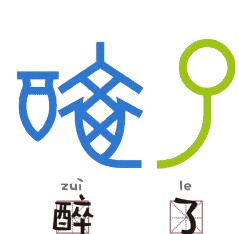【仲英学者】醉酒的哲学

汉字“醉”是个会意字,从酉从卒,“酉”即“酒”,“卒”表示“极点”“极端”,因此“醉”的本意就是酒喝到极端,失去正常神智的状态。由“醉”所指的“饮酒过量,神志不清”的本意,又引申出沉迷、过分爱好、醉心、沉醉、陶醉的意思,比如很满意地沉浸在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沉浸意味着敞开自身、全身心的投入。因此,醉酒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摄入酒精过度的生理层次;其次是酒后意志不清的意识层次;第三是敞开自身的主体层次;第四是沉醉于世界之中的万物一体的存在论层次。
甲骨文
醉酒状态的后两个层次体现了其与日常状态的疏离,因此醉酒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维度,主要表现在对现代社会机械化个体生活节奏和生存方式的调整和均衡。现代社会盛行所谓的“苟活经济”(Ökonomie des Überlebens),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每个人都是不知疲倦、自我压抑的劳动主体,被庞大的经济体系和信息体系所支配和压制,都是“单向度的人”。我们无时无刻不被担忧无法苟活下去的焦虑所支配,只能以机械化的方式不断向前,就像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里那艘荷兰船只那样,没有航向,但也不能停泊靠岸,也无法保持静止,只能在茫茫大海上不停航行。
漂泊的荷兰人
然而,从技术和效率上看,这个压抑主体、单向进步的社会反而被视为积极而高效的社会,生命中的欲望和情绪、个体的差异等“消极”面向被边缘化,理性的日常、对效率的追求被视为主流,并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反过来形塑个体生存。在这个价值取向下,可复制、可替代的工业产品式的存在物成为这个时代理想的模型,而脆弱且有死的人则只能怀着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所言的“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生存。同时在这样一个流水线式的现代社会中,带着羞愧的个体总是被一种涣散的注意力所充斥,我们不得不在碎片式的多个任务、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筋疲力尽。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飘忽即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长久持存,连相对固定的关注都越来越难实现。与技术时代和工业产品的永恒相对,人类生活和世界都是短暂的,缺乏长久持存之物,这就是现代生活中的“存在”的匮乏,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由此转换成了个体的存在焦虑。如果我们回忆下海德格尔对于古希腊人“求知”的分析,对“存在”和世界本质的追问是要缓解人类面对无常命运的焦虑;那么今天当我们的生活变得碎片化而短暂易逝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被紧张情绪和烦躁不安所支配,这也变得很容易理解。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去魅作用,宗教再也无法平息我们的焦虑。在此,醉酒似乎是暂时消解焦虑的一种有效手段。醉酒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和纠偏的力量,通过醉酒,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人与世界的融合给了个体一种安全感。
普罗米修斯
除了缓解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存在焦虑之外,醉酒作为生命中的创造力之源,更有对抗技术时代中麻木涣散状态的力量。如韩炳哲所言:“生命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有积极面的生命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消极对于保持生命力至关重要。”醉酒状态就是现代社会中这样一种保持消极的面向,是对积极状态下涣散的注意力的克服。醉酒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身体和精神放松的方式,就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深度无聊”。一味的忙碌只是在流水线的重复,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的成果,而深度无聊的状态则是精神放松的终极形式,是个体脱离时代流水线、建构生活意义的过程。
醉酒的另外一层批判性意义在于对日常时间的克服。在日常生活中,主体保持着理性的清醒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日常意味着日复一日的按照一种众人接受的模式和习惯思考、行动,忽略个体差异、忽略独一性,这种日常的时间是无差别的、匿名的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在现代技术单向进步观的支配下,时间也是永恒均质地往前延伸的。这样一种日常状态是排斥死亡的,海德格尔称之为“沉沦”,此在的“向死而生”是对这种永恒技术时间的最终克服。而醉酒尽管没有“死亡”那样对生存有着绝然的巨大压力,但同样是对沉沦的日常生活和技术时间的挑战和背离,是一种回归个体生命的律动。它并不顺从日常中我们要面对的时间节奏和生存压力,与增量、增值、增长的压力无关,甚至要与不断增速的生活对抗,用一种身体状态捍卫个性。醉酒带给我们的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的“感官的革命”或者“新的感官系统”,尼采所言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对于线性时间模式下的致力于无限增加的现代技术生活而言是毁灭性的。正是在这种背离和毁灭中艺术式的创造性光辉得以展现,从这一点上看,醉酒才让我们回归个体生存的本真时间,构成另一种本真意义上“向死的力量”。而且,由于醉酒是可重复的,这种对抗可以被一再施行,构成一种对于技术生活的均衡力量而非彻底毁灭。毕竟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均衡而非死亡,才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和积极追求。
注:文中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
文中配图来源网络